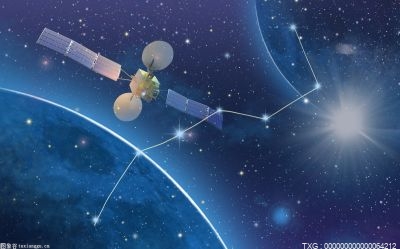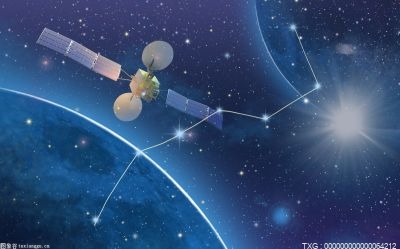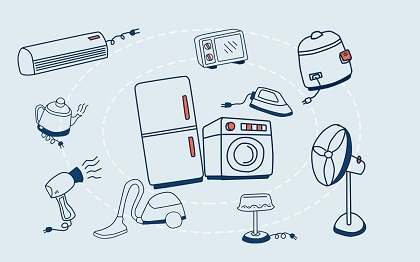作者对围棋的热爱因为互联网时代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的到来得以恢复和维护
年轻时候的一段日子围棋下得有点疯,每天下午似乎都围着棋盘。一间狭小的宿舍里,三个棋友轮换着捉对厮杀,构成所谓的“铁三角”。三个人水平不相上下,这肯定是“铁三角”结构稳定的重要原因。我与另一个棋友都在研究机构供职,可以自由支配时间;另一个棋友在外贸公司工作。他总是欺骗领导外出联系生意,然后一转身溜到我们这儿下棋。这个棋友远道而来,我们得客气一些,往往两个人陪着他对弈。我们各自下了一盘,他竟然下了两盘。外贸公司当时已经配备传呼机。腰间偶尔“嘀、嘀”响起的时候,他会冲到走廊上找一部电话,用一种我们深感陌生的语调抑扬顿挫地向领导汇报生意的进展,然后又冲回屋里趴在棋盘上。每日如此,多余的客套俱已免除。棋盘与棋子始终放在固定位置,进屋二话不说就开战,哪位想喝水不妨自我服务。搞外贸的口袋里偶尔会有一包好烟。他时常自顾自点起一根,仿佛专心致志于棋局,不会客气地问我们要不要也来一支。我们当然不予计较,下棋要紧。
年纪轻轻的只顾下棋,会不会有些玩物丧志?心里多少有些不安。搞外贸的提起另一个棋友的轶事。据说他在结婚的婚礼上被一个棋友当场拖走,躲到一个地方下了两天棋才回家。当时没有手机,新娘子一转身找不到新郎,不知发生了什么。这个新郎属于另一个棋友圈子,水平比我们高一些,大约已经业余5段。我们离业余5段还有不少距离,而且仍然记得老婆姓甚名谁,那就放心下棋吧,没什么可内疚的。我想不起这一段日子维持了多久。供职于研究机构的那位棋友后来赴日本定居,“铁三角”无疾而终。搞外贸的棋友从此杳无音讯,不知他是否已经晋升业余5段,抑或发财做了大老板?
“铁三角”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再纹枰对弈,周围似乎再也找不到合适的棋友。偶尔在电视上看到华以刚八段讲解围棋比赛,如同听评书的演义古战场形势。围棋日渐遥远,可是,围棋之道开始影响我的某些学术理念,譬如涉及“结构”问题。给几位博士研究生上课的时候,我时常带着遗憾的口吻说:可惜你们不会下围棋——我要用围棋作为譬喻。我建议慎用“深度”这种形容,好像只有挖地三尺才能从表象背后找到复杂的真理。围棋的棋盘仅仅显示一个平面的空间结构。但是,黑白棋子可以在这个空间结构形成无数可能,各种关系的复杂程度甚至是人类大脑无法负担的。每一手棋落入棋盘,原有棋子构造的既定关系或多或少遭受改变。所以,没有哪一手棋“本质”上是好棋或者坏棋。围棋不接受“本质主义”哲学。
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开始恢复我的围棋兴趣。登录围棋网站下一盘远比结交几个投缘的棋友容易。报上自己的围棋段位,网站可以迅速配对一个棋力相近的棋友。“小李飞刀”“西北剑客”“风轻云淡”“洛阳牡丹”——不论这些网名背后隐藏一张什么样的面容,轻点鼠标杀一盘就好。当然,纹枰对弈具有不可代替的快乐。知道输给哪一位,下一回复仇可以有明确目标;知道赢了谁就更快乐了——万一赢了一个声名卓著的作家呢?众人夸奖他天才的想象时,可以漫不经心地补充一句:唉,可惜围棋比我稍稍差了一些。我没有想到,文学圈子对于围棋如此热忱。计算是围棋的基本功。我曾经与一位数学教授聊天,询问是否对围棋感兴趣,收获的是一副不屑的表情。他说数学崇拜的是逻辑必然,逻辑必然不存在胜负。好吧,文学圈子不学无术,求胜心切。
2018年的时候,某家刊物在我居住的福州组织一场笔会,参会作家之中有一批文学界围棋精英。刊物策划穿插一场围棋比赛,列位作家夜间捉对厮杀,决出名次。我家的工作室成为赛场,排名证书由我用毛笔书写,并且蘸着印泥按上指印以示隆重。来自杭州的吴玄身手了得,我甘拜下风——可是,进入前三名理所当然吧?第一盘遭遇来自北京的傅逸尘,我毫无胜机。怎么搞的,一个如此强大的对手,事先居然没有一点情报?最终的排名恰恰是,傅逸尘荣获冠军,我被踢出五名之外——我所赢得的荣誉仅仅是,向傅逸尘发放自己手写的冠军证书。
这是一场开心的围棋盛宴,众作家相约来年再战。然而,来年迎来的是新冠疫情。惊慌,焦虑,不知所措。漫长的居家封控。何以解忧?惟有围棋。忘了是哪一位发现了“弈客”的围棋网站,众多作家棋友纷纷奔赴这个驿站注册接头,暗号照旧。作家棋友建立一个微信群,愿意下棋的时候一声招呼,二人携手飘入网络空间手谈一局。棋局可以发表在微信群里,以供众人围观。目前这个微信群多达七十余人,有时一日之内竟然上百条围棋评论,热得发烫。
居家无事,我也曾经登录“弈客”找一点感觉,挑战若干作家。手执一杆烂银枪拍马杀入:吾来也,何人出阵大战三百回合?踌躇满志,顾盼自雄,可是,战况丝毫不乐观。储福金兄乃是作家围棋界资深大佬,功力深厚,抬头望见城堡上“储”字大旗,我还是选择悄声绕开;吴玄个子不高,眼神凶恶,使一柄大锤,力大势沉,难以抵挡;傅逸尘刀法精湛,滴水不漏,攻不下来;郭红雷拜过名师,从他的手中讨不到便宜;张定浩瘦瘦的,是不是薄弱一些?不料他却是一个极为难缠的对手,屡屡从劣势之中突围而出,令人痛不欲生;最后只能找陈福民对垒。福民兄慈眉善目,行棋讲究大局,视野开阔,这种棋手或许会从手指缝之间漏下若干碎银子吧?事实再度证明,这是一种幻觉。与福民兄网络对局数十盘,似乎连三七开都难以维持——当然我是“三”。驰骋一番,奠定了中下游位置,心中暗暗扫兴。刀枪入库,马放南山,还是躲到后排休息一阵再说。
2022年炎热的夏季在厚厚的疫情阴霾之间划开一条裂缝。福州乘隙举办一场世界女子围棋大赛,中韩两国围棋女选手利用互联网对局。这是著名的传统赛事,聂卫平、王汝南、华以刚、华学明、常昊、俞斌、张璇等国手纷纷到场助威。大赛主办方别出心裁地邀请了一批作家棋友,组织一场作家棋友与围棋国手的联棋比赛。如同乒乓球的双打比赛,围棋联赛的规则是一位作家与一位国手搭档,双方对弈,一人一手。作家与国手之间实力悬殊,戏剧性场面陡然而生。国手弈出一手高招,作家不解其意,答非所问或者弄巧成拙是常见的事情。一阵眼花缭乱的抽签,吴玄幸运地与聂卫平搭档,我的搭档是王汝南。列位作家分别找到各自的伙伴。
我在棋赛开幕式的致辞之中说到一则趣事。很早就从电视机里认识了讲棋的华以刚八段,并且在人民大会堂的政协大会与他有过一面之缘。大会尚未开始,我端一杯水落座休息,忽而觉得邻座闭目养神的这一位仿佛哪里见过。我也稍稍闭目,猛然惊觉——这不是讲棋的华以刚八段吗?急忙睁眼,身边已经人去座空,心中久久怅然。此番再度相见,大慰平生。华以刚八段哈哈大笑。后来的座谈会,我们坐在一起,我从他那儿听到了许多围棋前辈的趣闻。
两天的围棋联赛,我与王汝南八段搭档获得亚军。作家棋友之中众多高手未能到场,我仿佛逮住了机会;当然,真正的原因是王汝南八段的提携。每一个围棋国手性格相异。有的人神情严肃,批评搭档的棋盘失误丝毫不留情面。王汝南八段一副好脾气,他事先笑眯眯地说,我下出的每一招都是好棋,尽管大胆出手。如此温暖的安慰让我心情稳定地恶手频出。一盘对局之中,王汝南八段下出一个局部妙手,周围诸多观战的专业棋手都看得出后续手段,只有我浑然无知,如同一个乞丐对于路边的金元宝视而不见。幸而那一盘最终获胜。否则,事后的复盘肯定令人痛心。
围棋联赛的冠军由聂卫平与吴玄联手获得。这似乎没有多少悬念。这一盘棋我缩手缩脚,仿佛穿了一件紧身衣。联棋比赛的一个奥妙是座位的排列。一方一手棋,甲方棋手出的卷子由乙方的哪一位棋手回答?这可能导致大相径庭的后果。不幸的是,我的上家恰恰是聂卫平聂棋圣。他并未使出哪些高深莫测的手段,每一招平凡无奇,稳如泰山,可是,我一筹莫展,无懈可击。闲常的时候,聂棋圣豪爽开朗,妙语连珠,对弈之际却神情肃然,不动声色。凝重的对局气氛之中,我突然转过一个念头:当年聂棋圣大约也是用这一副威严的表情对付武宫正树或者赵治勋。
颁奖典礼上,吴玄开心地领走了冠军证书。我当然要为我的亚军证书发表感言。我表示十分荣幸,能够败在聂棋圣手下——天下又有多少棋手能够杀到聂棋圣的门前,获得一个挑战的资格?在座的常昊听懂了我的吹牛,哈哈大笑。我有心气一气吴玄。他只是聂棋圣的小跟班,我可是堂堂正正的对手。
那一天晚上吃过饭,吴玄、绍武等人到我家喝茶下棋。我与吴玄再战一盘,又一次轻松地输了。复盘的时候,吴玄指出我的一个“定式”错误,并且告知人工智能软件对于这个“定式”的几种分析。“阿法狗”(AlphaGo)战胜李世石成为一个历史转折点。现在,所有的棋手都承认人工智能主宰围棋的绝对优势。各种人工智能软件不仅充当专业棋手的教练,甚至也可以屈尊指点我辈。吴玄等几位对局一丝不苟,一盘棋下完之后常常请人工智能软件评点一番,他们称之为“遛狗”。惭愧的是,我尚未购买这种软件——对于围棋缺乏足够的上进心。
尽管如此,我还是了解“阿法狗”们的威力。人工智能拥有强大的算力。棋盘上出现任何一手,人工智能可以迅速重新计算隐含的所有可能,并且预测这一手增添还是下降了胜率。根据宏观整体的精确蓝图评判每一个微小局部,这是人类无法企及的思想能力。当然,“阿法狗”们所谓的宏观整体以棋盘为界,计算的是棋盘之间棋子可能产生的全部组合方式;相对而言,人生面对的宏观整体渺无边际——谁知道历史的尽头在哪里?
无法企及人工智能对于整体蓝图的计算,我形成另一个赌气式的观念:放弃整体。我计划将计算收缩到一个又一个微小局部。只要评估这一手棋的价值超过对方的上一手棋,方案即可成立。对于一个棋手说来,评估一手棋负担的计算比评估整体要小得多。无所谓整体路线图,努力积小胜为终局的大胜,这种思想方法更为接近后现代哲学。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撤离历史总体论,专注于个别的游击战。
我将这种想法发到作家棋友微信群里,获得张定浩的点赞。瞧瞧,这就是有思想的人。张定浩的身份不仅是一个诗人,同时还是优秀的文学批评家。不久之后,吴玄的意见也过来了。他的意思是——他娘的,输棋还输得憋出哲学来了。
这小子的口气就是如此恶劣。当然,我只能容忍。谁叫我们都喜欢他那副赖叽叽的神气呢?
作者:南 帆
编辑:谢 娟
责任编辑:舒 明